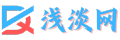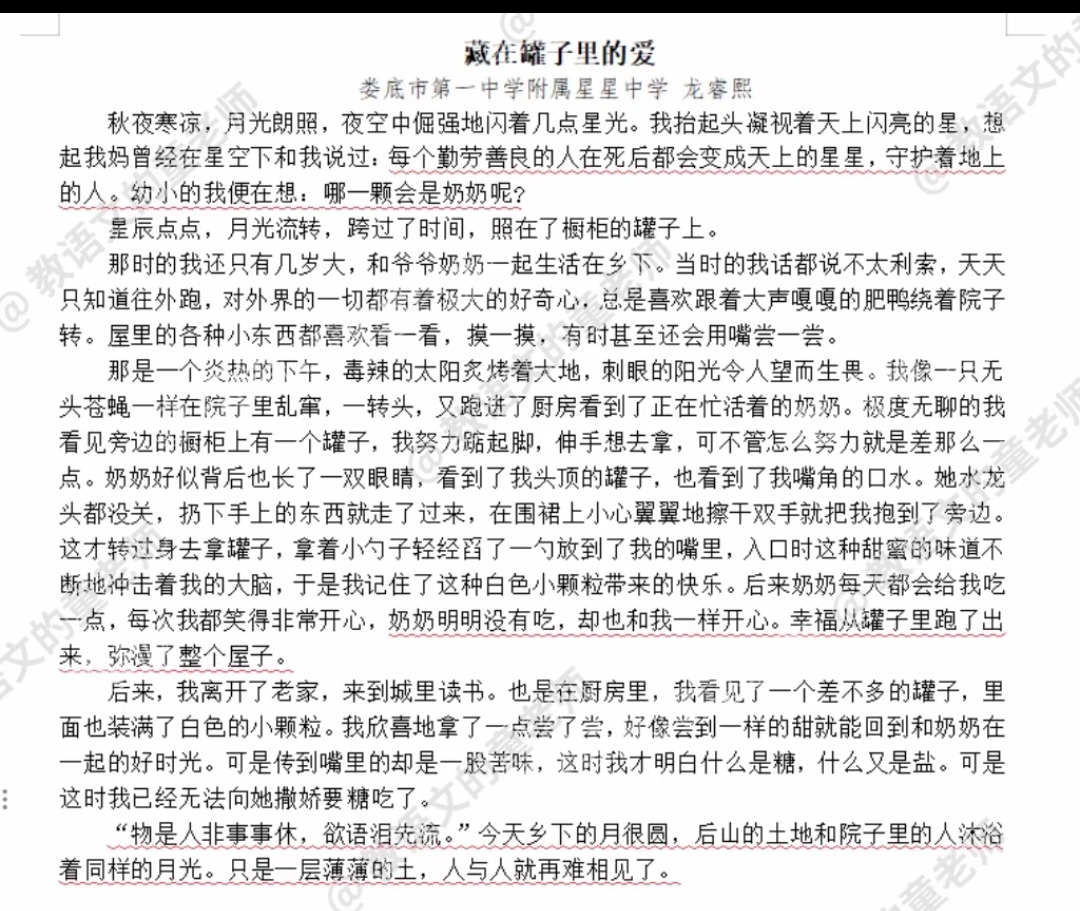故乡的根脉【思念家乡】
- EMO时刻
- 2025-08-24
- 136热度
- 0评论
故乡的根脉
当异乡的秋风卷起枯叶,如纸钱般飘零,我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。这风,终究不是家乡新乡的风。家乡的风,是裹挟着太行山松涛的清冽,是拂过卫河水面的微凉,是穿过玉米地时沙沙作响的私语——它吹过我的童年,吹过我的血脉,至今仍在我灵魂深处盘旋不息。
记忆的源头,是卫河畔那片青石板铺就的河滩。夏日里,河水清浅,阳光如碎金般跳跃在波光之上。我们这些野孩子赤着脚丫,在光滑的青石上追逐嬉戏,脚底被晒得发烫,却浑然不觉。河水温柔地漫过脚踝,沁凉如初吻,又似母亲的手抚过。偶有小鱼小虾惊慌地从脚边溜走,激起一串细碎的水花。岸边垂柳的枝条低垂,如绿色的帘幕,筛下斑驳的光影,也筛下奶奶在河滩边唤我回家吃饭的悠长声音——那声音穿透水声与蝉鸣,带着一种令人心安的暖意,仿佛能抚平世间所有躁动。
而新乡的滋味,是舌尖上永不褪色的印记。冬日清晨,街头巷尾弥漫着胡辣汤浓烈辛香的气息,那琥珀色的浓汤在锅中翻滚,胡椒的辛辣、面筋的韧劲、牛骨汤的醇厚,在寒风中交织成一张温暖的网,兜住每一个行色匆匆的过客。我常捧着粗瓷大碗,呵着白气,小口啜饮,滚烫的汤汁一路暖到胃里,也暖透了四肢百骸。还有那刚出锅的红焖羊肉,酱色油亮,香气霸道地钻入鼻腔,羊肉酥烂脱骨,入口即化,那浓烈的乡情滋味,是任何珍馐都无法替代的味觉图腾。更有那寻常巷陌里,母亲亲手蒸出的暄软白馍,掰开时带着热气,麦香四溢,蘸上一点咸菜,便是人间至味——这朴素的滋味,早已沉淀为我生命最深的底色。
新乡的魂,更在那厚重的历史烟尘里。辉县的百泉,碧波如镜,倒映着苍翠的山峦与古老的亭台。我曾漫步于泉畔,看“苏门山涌”石刻在岁月里静默,听潺潺水声仿佛在低语着孙登长啸、嵇康访隐的千古佳话。那水声,是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,洗濯着尘世的喧嚣。而比泉水更恒久的,是太行山的巍峨身影。它如一道沉默的屏障,横亘在北方的天际,山石嶙峋,松柏苍劲。山风呼啸而过,卷起松针的沙沙声,如同大地深沉的呼吸。这山,是新乡的脊梁,它用亿万年的沉默,托举着这片土地的沧桑与坚韧,也在我心中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如今,我漂泊在远方,城市的霓虹璀璨却冰冷,水泥森林里没有卫河的波光,没有青石板的温润,更没有那碗滚烫胡辣汤的烟火气。然而,每当夜深人静,异乡的月光如霜般洒落,我闭上眼,卫河的水声便清晰地在耳畔流淌,青石板的触感在脚下复苏,胡辣汤的辛香在鼻尖萦绕,太行山的轮廓在眼前巍然矗立——原来,故乡从未远离。
原来,故乡早已将它的根脉,深深植入我的血肉与灵魂。无论我行至何方,那卫河的水、青石的温、胡辣汤的烫、太行的骨,都如无形的脐带,维系着我与那片土地最原始的生命联结。纵使身在天涯,心魂却永远在卫河的粼粼波光中安眠,在太行山的苍茫怀抱里归家——这根脉,是生命之树最深的定力,它无声地告诉我:纵使浮生如萍,总有一方水土,以它全部的温度与重量,将我永恒地锚定在世界的中央。